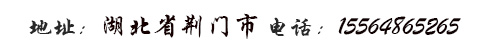穷险苦难的儿科医生,逃离还是坚守
|
《人间世2》第8集,以40岁的儿科女医生朱月钮为切口,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儿科医生的工作和生活。 他们将镜头对准了上海交通大医院,小儿危急重症医学科(PICU)。 故事以一场逃离展开…… 逃离 与朱月钮搭档了十年的老张,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走了,每每想到这,朱月钮就感到心里空落落的。 跟朱月钮的雷厉风行和偶尔暴脾气不同,老张从不跟人红脸,勤奋、认真、能扛事儿,是科室同事对老张的一致印象。 这样的人为什么走? 因为本科毕业、论文数量少的老张,医院「看不到未来」。 纵然他有能力,有经验,职业天花板还是触手可及。 科室主任朱晓东对此十分痛心。「他在我这边能上呼吸机,能做气管镜,能做血液净化,能做ECMO(体外膜肺氧合),能搞血浆置换,但是我们的体制导致他在这边看不到未来,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……」 老张并不是第一个逃离的儿科医生,科室不断有医生流失,「我们科室从建立到现在四年,四年辞职掉四个医生」朱晓东表示。 儿科医生流失严重,医院所要面临的问题,也是整个行业的现状。 年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届儿科城际间学术会议发布的《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(基础数据)》显示,年至年,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,人,占比为10.7%。 不仅流失严重,相比其他科室,儿科也面临招人难的困境,「其它科室两个名额,6个人报名,我们科室8个名额,只有一个人报名。」朱晓东主任伸出手指比划着。 年发布的《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》披露,国内儿科医生数量的缺口超过8.5万名。 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年底,全国儿科执业(助理)医师数为15.4万名,每千名儿童仅配备0.63名儿科医师,即约每1,名儿童能分到1位儿科医生。 而根据《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》显示,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每千名儿童的医师配比是0.85至1.3人,在美国,这个数字是1.6人。 中国儿科医生数量的缺口之大,原因大家都清楚。 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本是医生群体的共同特征,而儿科医生的情况则更甚。论辛劳程度,儿科不比任何一个科室轻松,而收入却长期处于行业的低洼带。 老张医院。 送别聚餐上,虽有不舍,但毕竟良禽择木而栖,同事们更多是为他高兴,只有朱月钮特别伤感,这伤感中,有对伙伴离去的不舍,也有对彼此相似际遇的感触。 按照朱月钮的话说,只因她「论文比老张稍多一点,学历稍微好一点」,所以还在「咬牙坚持」。 咬牙坚持 儿科,又称为哑科,因为小朋友还不会表达疾苦,这无疑为医生增加了诊疗难度。 对朱月钮来说,这种情况则更加明显,因为送来的都是危重症患儿,在查清病因之前,她得先想办法救命。 儿科的难处不仅表现在患者本身,跟家长沟通才是最困难的部分。 孩子是家里的焦点,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一大家人。而过于敏感的家长也给儿科医生的工作带去了困扰。 这天,朱月钮正急着赶往病房抢救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,走廊里的她正巧被一位家长碰上,该家长便追着她一路询问。 她的孩子是免疫缺陷病,并且高度怀疑结核感染,现在生命体征平稳,下医院明确诊断,之后再进行专科治疗。 结核属于传染病,按规定应该转入公共卫生中心,但家长却想转入普通病房。一方是心焦如麻的家长,一方是焦头烂额的朱月钮,争端一触即发。 「为什么不能转?」 「神经科不收。」 「为什么不收?」 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现在没空跟你讲这个事情,我有个病人要死了。」 朱月钮没想到,因为最后这句话,该家长去医务处投诉了,接着,她便陷入了无休止的争端漩涡。 家长不仅向医务处投诉了,还投诉到市民中心去了,既然不同意转到公共卫生中心,朱月钮便让其出院,可孩子耳朵和皮肤上的湿疹又让家长分外担心,不停地找她理论着… 从中午到晚上,朱月钮都被这件事所消耗——疲惫、烦躁、无语。但情绪归情绪,问题总归要解决,所以她还是马不停蹄地联系公共卫生中心的床位、联系转运的车辆,因为湿疹,她还请了皮肤科的专家来会诊。与此同时,她还要管理其他危重患者。 晚上8点40,家长终于同意将孩子转到公共卫生中心。与医院达成和解后的家长问朱月钮,「是什么精神支撑你做这个工作?」 看到家长不仅对她冰释前嫌,还表现出理解和关怀,她立刻收起疲惫、打起精神,笑答道,「因为我有个女儿啊,我要给她一个高大上的印象啊,人要努力工作才有饭吃啊!不说了,这是废话…」 闪光的日子 两床的孩子,脑部长了恶性肿瘤,在放疗的过程中,生命垂危,被紧急送到了PICU。 开刀、放疗…患者承受着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伤痛。家长更是难以接受现实,只要孩子的生命体征稍微平稳一点,马上就被他们送去放疗了。 在朱月钮看来,孩子的生命基本走到了尽头,家长的固执坚持不仅不会扭转病情,还会让孩子更加痛苦。 终于在一个安静的午后,朱月钮对家长说出了那番让她如鲠在喉的话—— 「如果但凡他没有治疗方案了,赶紧你陪陪他,陪伴他走过最后一程,他不会这么孤单,他就像一个树叶飘在外头了……」 病房里时常有患者离去,对见证者来说,伤痛、死亡、恐惧,像液体流过容器一般趟过他们的记忆,有人能自行消化,有人却难以承受,特别是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。 同病房患者的死亡在一位小姑娘心中投下了阴影,她坚决地表示,「宁愿在家疼死也不进这里了」。朱月钮曾告诉她,只要拉出大便就可以离开,她便急匆匆地跑去告知,说自己拉出来了,可以出去了吗? 这番童稚的话语让朱月钮哭笑不得的同时,也给她添上了一层挥散不去的隐忧。小姑娘年龄不太小,不能像对付儿童一样靠哄,于是她开启了一场温情又富有哲理的谈话—— 「有的时候树上的叶子会掉下来,但有的叶子还是长着的。那些掉下来的叶子是因为它们坏掉了,或者没有养分了,所以才掉下来。但更多的叶子会长在树上,你是会长在树上的那个……」 因为PICU的独特性质,这里的医生总是拧紧发条,时刻备战,但也有类似时刻,让朱月钮卸下警惕,重新审视医生的责任,享受作为一名医者的温情。 这样的时刻还有——抢救回一条生命,收到出院小患者寄来的礼物,家属的理解与支持…它们是宝石,让庸常的日子闪闪发光。 诚如朱月钮在镜头前的坦言:「人的一生,绝不总是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它隐藏了各种忧愁、尴尬、苟且、伤痛。但我相信,医生可能比别的职业更容易找到存在的意义。」 坚守 职场上的朱月钮,有着一副精神上的盔甲,唯有10岁的女儿,能让她卸下盔甲,暴露脆弱。 女儿的成绩下降了,她很焦虑,因而给女儿辅导功课的时候,总免不了发脾气。但正如她老公所说,「你都没有管过她,凭什么骂她」。 对女儿的亏欠成了朱月钮的一块心病。 她自己也矛盾地总结:「一边是翻江倒海的生死,一边是女儿一去不返的童年。」儿科医生和妈妈,她只能当好一个。 一次,一位暴发性心肌炎的患者被送进PICU,朱月钮和科室的医生连续守了个小时后,终于,患者的心脏可以独立跳动了,ECMO撤掉了。 该患者和女儿一样大,都是10岁,在办公室休憩的间隙,她突然想起与患者年纪相仿的女儿,竟难以自持地哽咽了起来。 「我(为女儿)做的就那么多,做不了什么事情…女儿这两天考试都没有人关心她……」 除了女儿,对于40岁的朱月钮来说,更头疼的是9月份的高级职称评定。要在这个行业里混,就要遵守这里的规则,「挤不进这个洪流,你就不适合在这生存,那就走,离开。」 朱月钮依然清晰地记得去年评副高时,本以为稳当了,结果名单上却没有自己的失落。 评职称的硬要求是科研文章,但儿科医生的短板就在这里——人手短缺的儿科,医生几乎没有时间搞科研。 而「搞临床也是救人,搞科研也是救人」,这一端是真切的病痛,那一端是渺远的研究成果,面对这样的天平,我想每一位医生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。 年9月13日,是高级职称评定答辩的日子,患者的感谢信、感谢锦旗,朱月钮都一一拍下,作为自己工作表现良好的证据,一遍遍演习着答辩的开场白,紧张地像个第一次登台演讲的小学生。 而这却不是朱月钮的第一次,从年到年,这已经是她第五次参加副高晋升了。 预答辩时,为了增加她的胜算,领导让她一定要说这是她第五次上台了。她坚决不肯,笑着说,「我就是不要讲这句话,太丢人了!」。(责编:joy)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erchaa.com/ecjb/629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茶里加一物,功效翻倍,1杯顶13杯,原来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