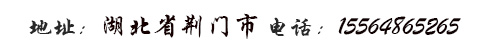茶膏的分类和孩儿茶的秘密
|
医院治疗白癜风费用 http://m.39.net/pf/bdfyy/bdfrczy/ 众所周知,明代谢肇淛《本草纲目拾遗·木部》“普洱茶膏黑入漆,醒酒第一,绿色更佳。消食化痰,清胃生津,功力尤大也。……普洱茶膏能治百病,如肚胀受寒,用姜汤发散,出汗即愈;口破,喉颡受热疼痛,用五分噙。皮血者,研敷立愈。” 可是普洱茶业复苏近二十年来,不少人亲手熬制、买卖和泡饮了不少的茶膏,想必不少人都从实践中发现,其所熬制的茶膏的实际功效,与上述所载的功效严重不符,相差甚远。这种区别或差距的原因,究竟出在哪里呢? 原来是历代药籍或史料中都不仅把“两类茶膏”相混淆,而且,因茶膏又称“孩儿茶”,与“儿茶”相混淆,致使几种物品混淆不清。 清代《普洱府志·物产·食品》载:“乌爹泥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:‘出南蕃爪哇、暹罗诸国’,今云南、老挝、暮云场地方造之。云:‘细茶末入竹筒中,坚塞两头,埋污泥淯中,日久取出,捣汁熬制而成。块小而润泽者为上,块大而焦枯者次之。’”其中只言半语都未提到它的滋味是否“苦涩”,证明它已不带有苦涩味。从末句“块小而润泽者为上,块大而焦枯者次之。”可知,本来同样是“细茶末入竹筒中”,却分为“块小”和“块大”,是因为细茶沫受潮结团,发酵生热后松散,这是隔绝空气,封闭“发酵”的“发酵茶膏”的工艺。只因封闭程度的区别,“块小而润泽者”是封闭良好,未渗入空气的无霉变“纯发酵茶”熬制成的“发酵茶膏”,并非“霉酵”茶熬制的“霉茶膏”,所以其品质“为上”(即优良)。而“块大而焦枯者”,则是因封闭不严密,未彻底隔绝住空气,有空气渗入,使茶末霉变而“焦枯”。由此熬制成的茶膏,是带霉变的“霉酵茶膏”。其内的“污泥”是习惯性语误,实际指“淤泥”。 经笔者近十七年来的间断性反复试制,制作成功所得到的“纯发酵茶膏”的亲身冲泡、饮用和外敷验证,充分证明上述引文所记载的“乌爹泥”即“纯发酵茶膏”的功效是真实、有效的,而且是神奇的。而其滋味里已经没有丝毫的苦味,仅微带涩味,微酸味。 清代张璐《本经逢原·土部》:“孩儿茶,一名乌爹泥,性涩收敛,止血收湿,为金疮止痛生肌之要药。白磁器研细水飞,敷痈肿,可代针砭。又点目去翳。”并且引用同内容的约汉代《本经·土部》内容:“孩儿茶,一名乌爹泥,性涩、收敛,止血、收湿,为金疮止痛、生肌之要药。白磁器研细水飞,敷痈肿,可代针砭。又点目去翳。”其中所称既与前者同名“乌爹泥”,又称“孩儿茶”,而且也同样是只言半语都未提到它的滋味是否“苦涩”,证明它也不带有苦涩味。虽然未提发酵工艺及其过程,也理应与前份记载所指者为同种物品。 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土部》:“乌爹泥,亦名孩儿茶、乌垒泥。制法:用细茶末装入竹筒中,坚塞两头,埋污泥淯中,日久取出,捣出捣汁熬制,即成乌爹泥。原产地在云南一带。气味:苦、平、无毒。”其中的名称,也既有“乌爹泥”和“乌垒泥”,也有“孩儿茶”。前两名,应是异地或异族对“爹”和“垒”的发音差异。虽然也有与“纯发酵”工艺及其过程几乎等同的“制法”陈述,但是明确记载着其“气味:苦、平”,也就是滋味苦。这与由所述工艺实际得到的膏状物的实际滋味严重不符,相差甚远。理应属于物品类别与所述工艺不相对应,不相符合的其它物品。 一、不会是上述“纯发酵茶膏”,就连“霉酵茶膏”都不是,因为“纯发酵茶膏”和“霉酵茶膏”都不会有“苦味”。二、不会是以明、清及其以前的“古六茶山”生活用茶为原料的不经发酵工艺,直接以新近茶为料的“非发酵茶膏”,因为以“古六茶山”生活用茶为原料,即使不经发酵过程的新茶膏,也不会有“苦味”。三、可能是以瓜芦或其杂种新茶为原料,而且未经过发酵过程,直接以瓜芦或其杂种的新“茶”熬制而成的膏状物。四、可能是保山及其周边等地“儿茶”,因“儿茶”名称与“孩儿茶”相混淆,把以豆科植物“儿茶”为原料制成的“儿茶”,与三类“茶膏”相混淆。其中的“污泥”,是对“淤泥”的习惯误称。而“淯”是指有淤泥的水潭,后人讹误为“沟”。 清代.汪昂《本草备要·金石水土部》载:“孩儿茶,泻热,生津,性涩收湿。苦涩,清上膈热,化痰、生津,止血、收湿,定痛、生肌。涂金疮、口疮(硼砂等分),阴疳、痔肿。出南番,云:是‘细茶末。纳竹筒,埋土中,日久取出,捣汁熬制而成,块小润泽者上,大而枯者次之。’” 清代吴仪洛《本草从新·火类土类》:“孩儿茶,泻热生津、涩、收湿.苦涩微寒.清上膈热.化痰、生津.止血、收湿.定痛、生肌.涂金疮、口疮(硼砂等分)、阴疳、痔肿.出南番.以细茶末纳竹筒.埋土中.日久取出.捣汁熬成.块小润泽者上.大而枯者次之。以上土类。” 清代张秉成《本草便读·土类》:“孩儿茶,苦涩且微寒.能点痔而止血.热痰仗清化.可定痛以生肌.。” 这三份记载中,虽也有“纯发酵”工艺及其过程的陈述,末者内还明确表明“胶滞之物”,同时,其所说的功效“涂金疮、口疮(硼砂等分),阴疳、痔肿”和“生肌、口疮等药,皆外治为多”等功效也与“纯酵”或“霉酵”茶膏相吻合,但却都指出其滋味“苦涩”。即使不是以豆科植物尖叶为原料制成的“儿茶膏”,也只会是以瓜芦或其杂种新茶为原料,而且未经过发酵过程,是直接以瓜芦或其杂种的新“茶”熬制而成的膏状物。其中的“污泥”,也是对“淤泥”的习惯误称。 清代黄宫绣《本草求真·泄热》:“孩儿茶(专入心肺)。味苦、微涩,性凉、无毒。功专清上膈热。化痰、生津,收湿、凉血、生肌。凡一切口疮、喉痹,时行瘟瘴,烦燥、口渴,并一切吐血、衄便、血痢,及妇人崩淋、经血不止。阴疳、痔肿者,服之立能见效。出南番,是细茶末入竹筒。理土中。日久取出。捣汁熬成。块小润泽者上。大而枯者次之。真伪莫辨。气质莫考。用宜慎之。” 此记载与前几份不同的是其中指出了“真伪莫辨。气质莫考。用宜慎之。”这的确是事实!的确应特别注意!因为本文的核心内容,也就是“四种物品”的混淆问题。 明代谢肇淛《滇略·版略》载:“孩儿茶之属,皆流商自猛宻、迤西,数千里而至者,非滇产也,而为滇病最甚。然《后汉书》已称:‘永昌出’。”其中,“迆西”是指“陇川”(德宏)。其意思与前文所引的清代《普洱府志·物产·食品》所载:“乌爹泥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:‘出南蕃爪哇、暹罗诸国’”相一致。虽然,古代由暹罗(泰国)、莽缅(缅甸)、车里(版纳)达滇的通道,但除了“贡象下线”即车里经思普、楚雄道,还有“贡象上路线”即德宏经永昌(保山)和楚雄道。因而,凡是产无“苦味”的茶膏者,除了“爪哇”(印尼)以外,“暹罗诸国”理应是指时而属于这,时而属于那的车里。也就是说,由猛密(今缅甸)和陇川(德宏)经永昌(保山)的“孩儿茶”或“乌爹泥”(即茶膏),也可能是产于车里“六茶山”。但“古六茶山”明、清及其以前所产的“乌爹泥”或(茶泥)即茶膏,无论是“发酵茶膏”还是“非发酵茶膏”,都不会有“苦涩味”。因此,凡是有苦味的“孩儿茶”或“乌爹泥”,只会是“爪哇”等地所产的以瓜芦及其杂种为原料的“非发酵茶膏”。 另外,末句“《后汉书》已称:‘永昌出’。”者,除了可能是把经过陇川(德宏)贩运来的“孩儿茶”,因由永昌入滇而误载为“永昌所出”以外,还有可能是指永昌(保山)本地所产的以豆科植物“儿茶树”的嫩尖、嫩叶制作的“儿茶”,也会被误解为“孩儿茶”。 就如《本草纲目》云:“‘乌爹或作乌丁,皆番语,无正字。’古人误以为本品。乃‘细茶末熬制而成’,故名‘儿茶、孩儿茶’。”也就是把“细茶末熬制而成”的番语所称“乌爹或作乌丁”,误解混淆为永昌(保山)所产的用豆科植物“儿茶树”的嫩尖、嫩叶制作的“儿茶”或“孩儿茶”。 清道光《普洱府志·物产·食品》“熬膏外,则蒸而为饼,有方有圆。”其内所说的是“普洱茶膏”,在明、清两代,它只有“六茶山”所产者,但是可能包括“纯发酵茶膏”(含霉酵茶膏)和“非发酵茶膏”。 清吴大勋《滇南闻见录》:“每年备贡者,有团有膏。”和“匣盛茶膏”其中所载的是作为普洱贡茶的茶膏,理应都是“纯发酵茶膏”。 清吴大勋《滇南闻见录》也载:“每年备贡者,有团有膏,思茅同知办团饼”, 其中,“每年备贡者,有团有膏”是指普洱贡茶,除了茶膏和瓶盛的“蕊茶”及“芽茶”以外,紧压茶全部制为团。就如清阮福《普洱茶记》所载:“每年备贡者,五斤重团茶,三斤重团茶,一斤重团茶,四两重团茶,一两五钱重团茶,又瓶盛芽茶、蕊茶,匣盛茶膏”。“同知办团饼”中的“团”就是紧压茶团;而“饼”,并非“茶饼””,而是指“缎匣所盛”的茶膏饼。 总之,“孩儿茶”,名称包括“乌爹泥”(纯发酵或杂发酵茶膏)和豆科植物“儿茶”。其中的““乌爹泥””包括以生活用茶为料和医药用茶为料的“纯发酵” 与“杂发酵”茶膏。此外还有以生活用茶为料和医药用茶为料的“非发酵”茶膏及“儿茶膏”。其中真正有上述功效的是以生活用茶为料和医药用茶为料的“纯发酵”与“杂发酵”茶膏,此两者和以生活用茶为料“非发酵”茶膏都应无苦味。纯发酵,非今熟茶。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erchaa.com/ecgj/1080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运动展览赏景甜品,包揽申城秋日的吃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